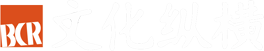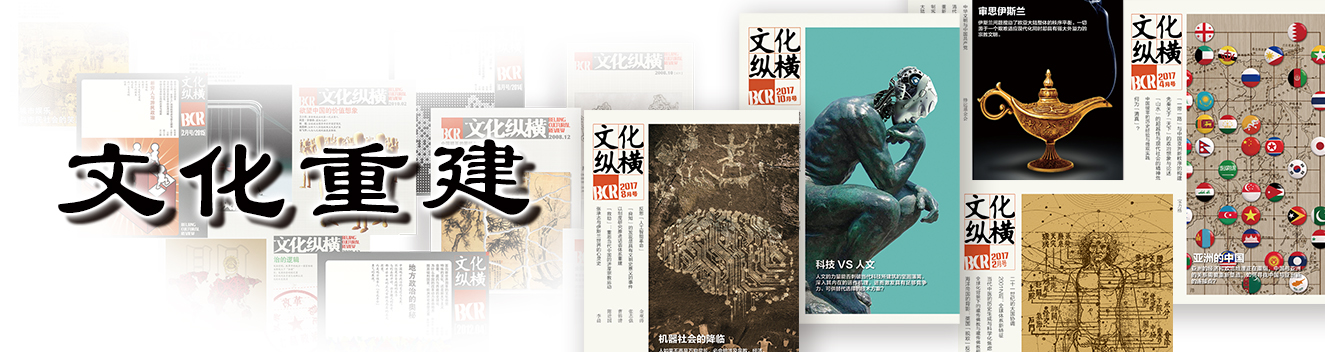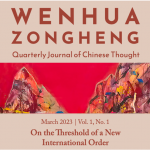? 沙燁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導讀】
充滿挑戰的2020年即將過去,未來的道路依然艱險。本文作者沙燁先生指出,中美科技戰將是一場至少長達十年的斗爭。企業將是這場斗爭的市場主體。他預測,斗爭的過程將驚心動魄甚至充滿挫折,但得益于中國的規模和活力、全社會支持、組織和執行優勢,最終中國企業將全面勝出,十年內世界上市值排名前100的企業中,中國企業的數目將超過美國,并占總數一半以上。但必須關注的是
,中國仍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僅千余元,粗略計算,中國400個富豪的財富相當于6億中國人兩年以上的收入。他指出,
那些曾為改革開放奠定重要物質基礎的人才和勞動力,貢獻了巨大的“犧牲紅利”,卻未必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受益者,
價值創造者和利益獲得者完全錯配。就此而言,商業不是最大的慈善,商業是最大的被慈善對象。
未來解決貧富差距的關鍵,是實質性地推動收入分配改革。而中國企業家作為改革開放的“先富”群體,有必要深刻領悟張謇精神,與社會共擔“共同富裕”的使命和責任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
為沙燁先生在觀傳媒圓桌討論《危機之后中國企業的新時代》的主題演講,經沙燁先生授權發布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各位思考。
危機之后, 中國企業的使命是什么?
今天請了幾個好朋友來做這個論壇。我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投資人,先分享一下我的觀察和預測。
毫無疑問,中美科技戰將是一場至少長達十年的偉大斗爭。企業將是這場斗爭的市場主體。我預測,斗爭的過程將是驚心動魄甚至充滿挫折,就在上周,華為被迫出售了榮耀。但最終中國企業會全面勝出。中國企業將不但以規模取勝,更能夠占據高端價值鏈。十年內,世界上市值排名前100的企業中,中國企業的數目將超過美國,并占總數一半以上。
我的預測基于三點根本的原因。
第一,中國的的規模和活力。中國不僅疆域廣闊,人口眾多,還有豐富多樣的文化和社會發展階段。我們不像美國是移民國家,卻有很多移民城市。這種規模和多樣性的交融能產生更大的經濟活力,也培育出大批充滿競爭性和動物野心的企業家。在座的幾位就是很好的例子。和美國比,中國是八九點鐘的太陽。
第二,全社會對企業發展的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包含了戰略性中央政府、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競爭性企業系統的三維市場體制。中央政府通過長期主義的總體規劃和基礎設施投資,地方政府通過向企業資源和政策傾斜,共同推動了企業的超常增長。電商巨頭阿里巴巴背后是中國領先于多數發達國家的移動網絡、公路網和鐵路網。
第三,在由互聯網帶來的全球信息化時代,中國文化中在組織和執行方面產生的優勢,將遠大于我們在創新方面可能存在的弱勢。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不要在創新領域迎頭趕上,相反我們非常需要。但在信息化時代,創新的優勢被降低了。創新承擔大量的試錯成本,可創新一旦發生后,真正的勝利卻往往被那些能夠成功產業化的企業奪取。字節跳動沒有發明AI算法,卻做出了全球最成功的AI應用:抖音和tiktok。中國文化中在組織和執行上的結構性優勢,最終將讓我們在產業化上勝出。
(沙燁先生在演講現場)
當然在預測中國企業的光明前途后,如果沒有進一步思考企業和社會的關系,就很難做一個稱職的社會主義國家投資人。
去年在這個講壇上,我提出過“犧牲紅利”的概念:中國今天所有的財富都離不開無法被定價的80年“犧牲紅利”。這包括先輩們為擁有一個獨立的國家主權和穩定的政治環境做出的生命的犧牲;也包括建國前三十年為完成社會變革、工業基礎的建設,和人力資源的積累,兩代人不計個人得失所做的犧牲,還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為響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勞動人民用汗水、辛勞和骨肉分離,為市場經濟的起飛所作出的犧牲。
在這里,我想進一步和大家思考企業以及市場經濟和社會的關系。
什么是市場經濟?市場是商品和服務建立價格并完成交易的過程,而市場經濟是指通過市場來配置社會資源的經濟形態。很多市場派經濟學家迷信于一個概念叫自我調節的市場,認為市場產生的結果有天然的正當性。可惜他們是錯的。之前我用犧牲紅利的概念已經說明,市場經濟從來無法孤立地存在。
從某種程度上,市場經濟是基于社會這個廣闊主體上的一個財富游戲。這個游戲以可貨幣化的交易作為基本單元,通過無數次交易的迭代達到財富的積累和轉移。而經濟的金融化更讓市場的參與者通過數學公式產生出更多可交易的虛擬結構,比如股權、債券、期權等等,并從中獲得豐厚的利益。經濟的金融化讓財富創造不再需要和實業有任何關系。
為社會創造最大價值的群體和從這個財富游戲中獲得最大利益的群體并不直接相關,有時候還恰恰相反。比如2008年造成世界金融危機的銀行家們對社會沒有創造什么正價值,相反他們摧毀了巨大的財富,但他們個人卻從市場中獲利豐厚。
我一直認為,市場經濟這個游戲從來不是孤立的,它從屬并依賴于社會和政治。市場經濟經常從社會這個土壤中吸取價值,并把這些價值貨幣化后進行利益分配。就如我們的領導人所說:“任何企業存在于社會之中,都是社會的企業。”
沒有比今年新冠疫情更好的例子能說明我的觀點了。成功治理疫情無疑是在激烈的中美競爭中對中國的巨大利好。如果把中美競爭比作騰訊阿里雙巨頭間的競爭,騰訊突然全員上下拉了兩年肚子,你說這還怎么打?那么治理疫情最大的功臣又是哪些人?首先是我們的政治決策者。就如我的合伙人李世默曾經寫道:武漢乃至湖北大規模封城的決定只有最高領導人一個人能定奪,所有后果也只有他一個人來承擔。這個決定拯救了整個國家。當然還有我們千萬萬萬最可愛可敬的醫護人員、解放軍戰士、社區防疫人員、快遞小哥、環衛工人和志愿者。是他們讓我們免于歐美正在經歷的社會災難。
疫情恢復后,經濟復蘇股市大漲,龍頭股、科技股成為最大受益者。不出意外,今年中國又會多出上百個十億級美金富豪(billionaire)。據最新的福布斯報告,今年上榜400位富豪總財富從一年前的1.29萬億美元飆升至2.11萬億美元,增長了8,200億美元。與之相比,美國400富豪榜上榜者的總財富只增長了2,400億美元。這些顯然受益于中國對疫情的控制。但是那些為我們成功抗疫的英雄們,他們并不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受益者。2020新冠疫情大考年,價值創造者和利益獲得者完全錯配。
在這里,商業不是最大的慈善,商業是最大的慈善對象。犧牲紅利正在進行時!
再由此擴展。市場主體的核心參與者最關注的往往是利益分配,而市場經濟外圍的社會角色卻往往關注的是價值創造。當一個公司招募新的CEO或者高管時,他最想知道的往往是他能有多少股份或期權。但是你能否想象省委書記和地方政府商談,中國經濟增長部分中有多少比例可以歸他自己?同樣,你能否想象一個救死扶傷的醫生和病人談判這條生命的貨幣價值,或者一個誨人不倦的教師和學生家長談判這個孩子前途的貨幣價值?因為真正的價值往往受道德約束,無法被簡單貨幣化,而社會道德也不允許這些價值被完全貨幣化。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這個矛盾我的理解是:隨著中國企業的不斷崛起,市場經濟中,科技和金融的發展讓一小部分人對財富壟斷式的擁有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初心和理想的矛盾。前面講到中國富豪榜前400總財富2.11萬億美元,今年5月份李克強總理在人大記者會上強調,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簡單算下數字的話,400個富豪的財富相當于6億中國人兩年以上的收入。
怎么能緩解這個矛盾?在中央關于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遠景目標建議中,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
在中國近代的實業家、教育家張謇身上,我們也能看到國家領導人對企業家們的期待。11月12日,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期間,曾稱贊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時,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回到今天的議題,危機之后,我的預測中國企業將愈戰愈強。同時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社會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也將日益明顯。我期待中國出現更多張謇式的企業家。我相信社會主義會給我們答案。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為沙燁先生在觀傳媒圓桌討論《危機之后中國企業的新時代》的主題演講,標題為“危機之后,中國企業的使命是什么?”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