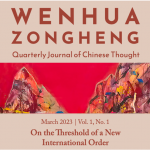? 周安安、吳靖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新聞與傳播學院
【導讀】 近年來,各種關于社會和時代變遷的影視作品層出不窮,形成“新主流文藝”浪潮。這類文藝作品超越此前的“主旋律”作品和市場化文藝,重構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敘事,具有史觀重建的重要意義。根據 作家阿耐同名小說改編的影視劇《大江大河》,正是此類文藝作品的典型代表,這部電視劇從不同的視角展現了改革開放先行者們在時代變革浪潮中的探索與浮沉。
本文認為,《大江大河》突破英雄主義、個人主義的敘事模式,從大眾文化層面,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作了一次嘗試性的闡述。影視劇從兩個方面展現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生產方式的重組進程。第一,國有企業被視為技術發展引擎。技術型干部宋運輝的命運也與三次技術改造緊密聯系在一起,過去國有企業和工人的困頓落寞形象,得以煥然一新,而這也從微觀視角展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歷程。第二,集體化作為鄉村工業化的道路。小雷家村鄉鎮企業的發展,既關乎鄉土社會內部如何處理個體與集體的發展問題,又涉及基層行政單位在經濟發展中如何協調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獨特的本地工業化由此展開。
時下,中國的改革開放仍在進行之中,對文化與社會觀念變遷的長時段觀察,將為今后的道路選擇與發展提供更多靈感與思考。歷史化敘事的重構,遠不僅是一次對過往的經驗性總結,更是一次重塑未來歷史的嘗試。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6月刊(第3期)第97-103頁,原題為“重述改革開放史:《大江大河》的突破” ,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重述改革開放史:《大江大河》的突破
在拉開一定的歷史距離后,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經驗在當下開始被重新對象化。2018年以來,大眾文化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多敘述改革開放經驗的作品,這些作品涉及對中國20世紀80-90年代歷史經驗的再理解,其中最為典型和豐富的一部,是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獻禮劇——《大江大河》。該劇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生產方式的重組進程為核心線索,獲得了叫好又叫座的成就,成為普通觀眾,尤其是年青一代熱烈觀看、討論和贊美的文藝作品。
作為一部主旋律作品,《大江大河》主要在兩個層面突破了傳統主旋律作品對中國道路描述的局限:第一個層面的突破是在進行主旋律敘事時,不再僅僅停留在對革命史和英雄人物的歷史追溯,而是正面描述了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社會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歷程;第二個層面是在大眾文化層面突破了中國改革開放史的敘事范式,將國有大型企業看作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推進工業化進程的中流砥柱,并將農村發展放置在建設集體經濟的脈絡內部,一改過去將改革開放史講述為個人主義的企業家精神、西方先進管理經驗的傳播、農民工在南方外貿工廠打工改變命運的故事。今日,中國生產與生活世界的公共議程已經發生了變化:在生產層面,大型國企在全球高新技術行業的話語權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公共議題;在生活層面,地方、小城鎮和農村作為倫理共同體的重要意義得以彰顯。《大江大河》對中國20世紀80-90年代的經驗重述,也正著重于這兩個方面。
▍大型國有企業作為技術發展引擎
在以往涉及商戰和職場的影視作品中,國有企業的形象被淹沒在新興經濟部門和企業家創業的英雄敘事的光環之下,通常是作為低端生產力和失落群體的生存背景一閃而過。而在一些具有歷史懷舊性質或者反思性的藝術電影中,國企衰敗、工人階級的困頓與悲歌,以及這一階級遭遇的歷史背叛是最核心的信息輸出。很長一段時期以來,在公共傳媒中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的敘事里,也幾乎找不到來自國有企業的案例與報道。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初創時期為中國的自主工業化和國家的能源、科技與軍事安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則在基礎設施建設、核心技術創新和制造業強國的打造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由于前三十年的敘事傳統,主旋律作品對第一個階段的敘述有所積累,但對第二個階段則缺乏相應文本。自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以來,中國在電力、交通、通信、航天、化工、醫藥等領域的核心科技能力和制造業的強勁韌性,在大眾傳媒中得到了“井噴式”的傳頌,導致人們在由文化作品提供的觀念和現實存在的現象之間出現了一種認知落差。
《大江大河》的文本則填補了這種認知落差。電視劇第一部講述了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老國企如何在不觸碰所有制改革的前提下,引進西方先進技術、進行管理現代化和面向市場經濟進行改革的故事;第二部則以新建化工廠如何引進技術、推進合資為主故事線,描寫了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從被技術封鎖到進入全球科技革命浪潮、汲取資源發展自身的歷程。通過敘述技術型干部宋運輝主持的三次技術改造,《大江大河》展現了社會主義企業的發展、運營和技術升級的一般邏輯、方法和問題。
第一次技術改造是宋運輝以基層工人的身份展開的。作為新分配到廠里的化工專業大學生,在被意外下放到車間“三班倒”后,熱愛技術的宋運輝對工廠設備的所有流程、運轉和維修情況產生了真實的工作熱情。在此基礎上,他全面記錄并計算了由于設備“跑冒滴漏”所造成的原料能源浪費和產能下降的情況,向廠領導提出暫時停產、讓維修科對設備全面整修之后再恢復生產的建議,并最終獲得了工人和管理者的認同。在這個過程中,工廠對技術邏輯的貫徹和堅持戰勝了來自官僚理性和工人文化的質疑,體現出在國企所有制下,流程優化與工人的權益、領導的政績其實沒有任何本質沖突。對設備的技術改造、維修和升級,對工作的認真不茍、精益求精,是一定條件下社會主義企業理性和企業文化的內在要求。然而,這種工廠共同體內部的一致性,在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大潮中,開始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分化而逐漸產生裂痕。這導致宋運輝接下來的幾次技術改造,變得充滿曲折而沖突迭起。
第二次技術改造是關于“單純擴大生產”還是“更新尖端技術”的技術路線爭論。當廠內的爭論被遞交到北京部委之后,宋運輝用當時國內化工業還無暇顧及的國際化工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和市場前景這一“大局觀”,挑戰了部委單純改善國內紡織消費品供給不足的“大局觀”。技術路線斗爭的雙方都有看似合理的戰略意圖。在這一回合中,宋運輝將技術評估與市場的動態需求聯系在一起,而非固守刻板的技術升級步驟和靜態的消費需求規劃,將市場與技術動態變化的理念引入了國企的日常管理思維之中。他試圖用最先進工業國的消費水平去看待和服務中國很快到來的買家市場以及技術創新的大潮,致力于將企業建設成未來技術的引領者。在《光變》一書中,路風將“技術追求”和“自力更生”總結為中國國有技術企業實現技術升級的兩大精神法寶,在本劇中,我們能感受到同一種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特有氣質與實踐方法論。雖然劇中技術升級的主要方式是“引進國外先進設備”,但是整個過程都是企業“以我為主”地對新設備和技術進行全面消化、吸收,掌握技術原理,在此基礎上與原有設備進行高效融合,并面向本地市場進行研發和創新。
第三次技術革新路線斗爭發生在全新規劃的東海化工廠。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國際資本開始積極探尋進入中國,中國國企也開始摸索更進一步的國際合作方式。新的路線斗爭涉及制度爭議:東海廠是僅僅引進國外先進設備,保留原有的“全國資”形式;還是開啟股權換設備的模式,用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和東海優良的基礎設施,吸引最先進的國際公司、生產線和管理資源的進入?原本一直支持宋運輝的部委領導路司長此時和他產生了分歧。宋運輝認為,一定要抓住國際資本青睞中國的機會,以最大程度的靈活性與其討價還價,必要時做出可控的讓步,用最短的時間把中國化工企業的技術、生產、管理、研發等各方面的能力提升上來,以形成自主發展的良性循環,可以和世界最先進的化工企業同臺競爭。而路司長卻指出,在迅速的開放中,不能只看到國際資本提供的機會,更要看到它們利用自身在行業標準、知識產權和底層邏輯上的壓倒性優勢,對第三世界企業的排擠和打壓——“否則第三世界也就不是第三世界了”。路司長認為,在全球化工企業已經形成了縱向整合、全產業鏈控制的“巨無霸”模式的條件下,中國企業在計劃經濟時代分屬不同地方、部委,條塊分割,也沒有應對國際市場的經驗,簡單放開各自為政的話,很容易產生重復建設、產能內耗的局面。因此應當先做行業整合,再與國際對手競爭。外資導致企業性質發生變化,很有可能在國內利益集團阻礙之上增加了國際資本干擾的變量。最終,宋運輝被路司長的政治邏輯說服。在經歷了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之后,觀眾對于這一技術路線分歧的理解會更加深刻。
▍中國鄉村工業化的道路:集體化
大眾文化對改革開放史中農民和小生產者的生存狀態、發展模式的講述,是被“分田到戶”和“雞毛換糖”兩種劇情模式所主導的。這兩種敘事的共同特點是,強調個人和家庭從集體之中脫離出來后、作為基礎經濟單位在市場交換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個人奮斗與家族糾葛是其劇情推進的主要動力。《大江大河》則一改這兩種敘事模式,將20世紀80年代興盛于蘇南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作為敘述主線,強調了“集體”作為一個經濟與生活組織形態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劇中小雷家村集體企業逐步發展壯大的故事,并非是一部沿著個人奮斗的商業邏輯而展開的企業史,而是一段依舊深嵌于血緣與地緣組織中的中國農民的生活史;而小雷家村村民參與集體化生產的過程,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處理自身生活世界里種種社會倫理關系的過程。
小雷家村建立鄉鎮企業的故事沿著兩條主要線索展開:第一條是關于村莊內部的社會關系,講述整個小雷家村在“鄉村能人”、村支書雷東寶的帶領下,通過處理改革過程中村莊內部種種復雜的人情糾葛,將村民個體在不斷變化的利益關系中始終團結為一個能夠同心協作的村集體;第二條敘事線索是,小雷家村作為最基層的行政單位,如何在發展過程中與鄉鎮和縣一級的地方政府互動,使得村莊的發展既能始終保持基層探索的靈活與彈性,又能始終不脫離大政方針。
作為農業立國的文明古國,如何應對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傳統社會結構在遭遇工業社會沖擊時表現出的脆弱性,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思考鄉村問題時的核心關切。費孝通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鄉鎮企業“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它和西方資本主義初期工業化的路子不同,它對農業不發生破壞作用,它對農民不產生貧窮化的后果”。鄉鎮企業得以建立的條件,除去區域地理條件外,在組織制度上則繼承了社會主義革命集體化的成果:“在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時,蘇南農民沒有把社隊工業分掉,而是保存了集體的經濟實體……蘇南農村工業化是在公社制度中啟動的,啟動資金來自農民的集體積累。”如今,站在三十年后回溯中國不同地區農村的發展歷程,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基層農村的發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是否能形成集體性的工業內生體制,是導致發展差異性的關鍵因素。
以往的農村群像戲多為倫理劇,觀眾對于農村生活的理解總處于一個靜態的情境,無法把廣大鄉村中人情倫理的變化與近四十年生產生活方式的劇烈變遷聯系起來。《大江大河》則反其道而行之,將劇中人物的個性沖突在集體生產的過程中展現出來。劇中最鮮活的人物是小雷家村村支書雷東寶,他身上豐富的層次感來源于其堅定的信念:帶領小雷家村人共同脫貧致富。小雷家村村民的認可是他全部經營活動合法性的來源,在這個過程中,他不能讓任何一位父老鄉親在致富列車上掉隊,同時也不能讓任何一位“能人”分走集體資產單打獨斗。這種集體理念既是雷東寶不斷前行的內在動力,也是他在不同利益主體間折沖樽俎時天然秉持的價值標準。作為一個鄉村帶頭人,雷東寶具有魯莽冒進的性格缺點,但這種“為集體利益計”的堅定觀念牽制了他性格中冒險和自我膨脹的部分,使他在日常行事中更多能體現出全盤謀劃、粗中有細的村莊帶頭人氣質。在劇作細節層面,《大江大河》著重反映了鄉鎮企業與村莊共同體之間的一體關系:一方面,鄉鎮企業賺取的利潤為村集體所分享;另一方面,企業基于鄉村的社會網絡和人際關系得以組織起來,并因村集體的身份得以在政策轉型期得到行政上的支持。
小雷家村的劇情中,得到著力描寫的另外一組主要關系是村集體和縣委領導班子的關系。在村莊帶頭人雷東寶所經歷的兩次人生低谷的故事情節里,其沖突焦點都集中在了縣鄉鎮領導班子的戲份上。在此,農村基層與國家呈現出市場主導工業化過程中的一種良性關系:在市場經濟的規則尚不明確時,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之間的關系是互助型的——鄉鎮企業大膽尋路,政府通過樹立典型的方式,確認基層實驗和國家大政方針之間的關系;而在市場規則逐漸定型、一部分基層實驗中的經營行為開始越過底線時,基層政府在掌握法治原則的同時,也和村集體之間存在著一種并非明確產權意義上的管理關系。
梁漱溟曾以“鐵鉤與豆腐”這一譬喻來說明近代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現代國家與農業農村之間的張力。對于當時以小農經濟為主要基礎的中國而言,官僚本位下的諸多建設事業,往往如“鐵鉤”傷害“豆腐”一般,最終淪為“勞民傷財”乃至于“橫征暴斂”。梁漱溟常被視為民國時期“以農立國”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本人其實對于工業化極為重視,尤為重視的是中國如何能走出一條超越資本主義式工業化下畸形城鄉關系的道路來。新中國建立后的不同歷史時期中,在不同的工業化條件下,“鐵鉤”與“豆腐”的張力始終若隱若現。而《大江大河》則著力呈現了一種梁漱溟理想中“安頓其身而鼓舞其心”的本地工業化,超越了以往“農民的個人主義解放vs面對市場毫無抵抗力的小農”這一組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中常見的農村敘事。
▍作為歷史敘述者的主流影視作品
《大江大河》第三部將于2022年推出,敘事時段可能會選擇從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到中國“入世”的這一段歷史時期,全劇的時間跨度約在20年以上。這種將日常生活史詩化的創作方式,給一直生活在持續性的觀念變遷中的中國觀眾提供了一種理解自身生活的長時段視野。全劇對改革開放前20年“工農商”三個群體在工業化歷程中的命運做了一番全景式的描摹。除了本文著力分析的國有大型化工企業與鄉鎮企業的發展史外,從第二部開始,作為商業貿易(私營企業主)人群代表的第三位男主人公楊巡的戲份也在逐漸加重。總的來講,這部電視劇以一種全景式的歷史展現方式和精準冷靜的現實主義視聽語言,將情感與現實、道路與體驗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邏輯自洽、形神兼備的敘事宇宙。
大眾文化對近四十年改革開放史的呈現多為兩種類型:其一是著力展現普通人通過個人奮斗獲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其二是以批判現實主義的眼光展現物質主義對于人心的侵蝕。然而,這兩種講述方式都忽視了技術生產過程的變遷、勞動模式的變化與世情人心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大江大河》在這一點上是具有突破性的,它展示了工業化社會中普通人的日常勞動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生活的變化。宋運輝主持的三次技術升級之所以能讓觀眾感到心有戚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符合從技術院校畢業的一代青年大學生的工作經驗:懷抱技術理想走入社會,而后在大型科層制企業復雜的組織文化里逐漸找到自己的技術能力與不同利益主體、不同戰略目標之間相契合的部分。雷東寶在和縣委干部的一段對話中,講起他所體認的小雷家村民的特點是:“最普通的農民,想自己多些,想別人少些,但想過好日子的心不輸給任何人。”也正是在這樣的普通人身上,才具有組織起來完成工業集體化的能量,讓村集體沒有變成在全球化體系中毫無議價能力的小農。這些都是該劇所提煉出的、過去四十年中最為正面的工業社會文化變遷的經驗。
在試圖對歷史進行全景式展示時,這部電視劇的敘事結構是有所取舍的。宋運輝部分所代表的“大型國有企業的工業化”強調的是國有企業如何走出一條科研-生產技術創新的路子來,對人事管理問題改制等敏感問題也進行了規避。小雷家村部分則將重點放在了村集體內外的組織化上,以“閑筆”點出了基層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問題,也用作為管理者的雷東寶的個人性格特征來回避了1993年產權改制后鄉鎮企業引發的制度爭議。但也正是由于這一取舍和回避,《大江大河》的精彩與不足才都獲得了某種具有當下意義的生命力。這部電視劇的動人之處也正與它試圖重新結構化歷史敘事的努力有關:這些重新被揀選的經驗既非移植自海外影視的技術性橋段,也不僅僅是少數人群的心路表達,而是一種能夠進入大部分普通觀眾內心情感的表達。四十年改革開放是一段尚待進行整理與總結的中國歷史經驗,而《大江大河》在大眾文化層面提供了一次可能的嘗試。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6月刊第97-103頁,原題為“重述改革開放史:《大江大河》的突破”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